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黑神话·悟空》这样的现象级产品
没有出现在创新最前沿的深圳?
深圳市50%—60%的人工智能企业集聚在南山区,而在南山区科创局,当前最为忙碌的部门可能就是人工智能产业办,这是一个成立于2023年的部门,如今“天天加班加点”。
年初,“杭州六小龙”出圈,深圳被外界不停地拿来和杭州比较,国内AI领域的竞争态势让深圳这座头顶“科技创新”光环的城市倍感压力。不少网民讨论:为什么像DeepSeek、宇树机器人、《黑神话· 悟空》这样的现象级产品,没有出现在创新最前沿的深圳?
其实,早在2023年,深圳市政府就成立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工作专班和人工智能战略咨询委员会。今年不仅继续推出一系列新政策,更是明确提出诸如“2026年人工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1万亿元”等具体目标。
面对新一轮人工智能浪潮,政府层面首先开展了“认知竞赛”。在DeepSeek的“大本营”浙江,拉开了一场对全省干部的人工智能专题大培训,为期4个月共10期课程,第一期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阿里云创始人王坚开讲,全省近30万干部在线上课,夜学AI。
3月31日,深圳成立了“十五五”规划专家委员会,这是一个由90位顶尖专家组成的“智囊天团”。90位专家中院士占比超过1/3,囊括了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扬生,鹏城实验室主任高文,深圳科创学院院长李泽湘,深圳医学科学院院长、深圳湾实验室主任颜宁等知名学者。其中专家人数最多的两个组是科技创新组和产业发展组,分别达22位、20位,意在争夺未来五年的高端产业发展话语权。
深圳自然不想错过人工智能产业的机遇,那么深圳又该如何破解当前的关键瓶颈?
 2024年6月26日,在深圳市南山区智园的优必选总部,工作人员对人形机器人进行测试。图/新华
2024年6月26日,在深圳市南山区智园的优必选总部,工作人员对人形机器人进行测试。图/新华深圳急了?
在DeepSeek引发的地方政府集体反思中,深圳被不断拿来与杭州对比,截至去年年底,深圳已经集聚人工智能企业2600余家,其中不乏腾讯、华为这样的大厂,但是并未诞生像DeepSeek这样有竞争力的大语言模型。
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在今年2月5日召开的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上指出,人工智能正在掀起产业变革,机器人时代逐步照进现实。广东兼具机电技术和数智技术两大优势,要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两大领域下大决心、集中发力,构筑高技术、高成长、大体量的产业新支柱。
随后,广东省省长王伟中到深圳市福田区、南山区、光明区调研,表示培育壮大机器人、人工智能、自动驾驶、低空经济、生物制造、量子科技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力以赴打造产业新支柱。
显然,深圳在广东打造人工智能、机器人两大产业新支柱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今年3月3日,深圳更是连续发布四份文件,事关科技创新生态和人才发展环境,其中两份与人工智能产业直接相关,即《深圳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5—2026年)》《深圳市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行动计划(2025—2026年)》。在去年7月底,深圳曾推出“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行动方案”,不到一年时间,这一方案完成迭代。
对于深圳连续出台针对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创新创业政策,有创业者向记者感慨,深圳开始“奋发图强”。而外界更愿意将其解读为“深圳急了”。
“宇树科技机器人技术确实有优势,但并非碾压竞争对手,有深圳机器人公司产品的平衡性甚至优于宇树科技,但是综合表现确实不如宇树科技。”有熟悉深圳机器人产业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宇树科技今年“出圈”有一定偶然性,春节前夕机器人赛道热度已然较高,随后宇树科技机器人在春晚登台表演,彻底出圈。
“其实优必选机器人此前已经多次登上春晚舞台。”他在言语间多少有些不服,“当前各家机器人公司展示的demo(样机),从空翻到舞蹈等动作,更多展现机器人‘小脑’的运动协调能力,但是深圳的机器人企业,如优必选更为关注机器人在工业场景中的表现。”
这种差异,展现出深圳在这一轮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机遇中更为注重应用。
“杭州的亮点在于大语言模型,无论是阿里的通义千问,还是DeepSeek,都优于深圳公司的模型。”有深圳本地投资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于缺少有竞争力的基座大语言模型,深圳企业可能并未感受到太多焦虑,无论基座大模型未来在哪些场景落地,似乎都很难突破腾讯、华为等大厂的壁垒,比如腾讯就在积极将DeepSeek纳入自身生态,而深圳企业在大语言模型领域的创新创业也更偏重应用。”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深圳在此前的“百模大战”中表现相对沉寂,并未诞生出有竞争力的大语言模型。
“大语言模型开发更多由出自高校的研究型团队进行。”一位深圳政府人士直言,深圳善于“搞钱”,结合产业是强项。使用哪个大语言模型并不重要,市场会选择那些成本低、质量高的大模型。模型还将不断迭代,DeepSeek也并非终点,大模型赛道可能会不断洗牌,但是唯一不变的是最终需要与场景结合。
“一些大模型公司往往只有模型,由于不掌握应用场景往往难以完成商业变现,从而成为‘炮灰’。因此深圳在制定一些人工智能产业支持政策时也更多关注应用场景。”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自己也会关注杭州的一些政策,但政策更需立足深圳自身特点制定。
虽有DeepSeek在前,但是深圳对于人工智能产业的“焦虑”可能并非源自缺少有竞争力的大语言模型。
作为深圳市南山区科创局副局长,董少林的另一个身份是南山区人工智能产业办副主任。“压力主要来自工作量增长。”董少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尽管人工智能产业办2023年便已成立,但是直到去年尚未独立办公,因为工作量有限,如今人工智能应用的爆发式增长正在颠覆传统产业。
“过去开发垂直领域AI模型需要数百万元投入,现在随着DeepSeek等技术的出现,大模型开发应用成本大幅降低,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积极布局AI应用,同时催生了一批专门帮企业做AI转型的服务商。”董少林曾在一周之内接触数家服务商,说明当前市场对于这类公司提供的服务有需求。
一体机的门槛很低,不到10张英伟达消费级GPU就可以组成一台能够运行DeepSeek-R1“满血版”模型的设备,价格可能低至十几万元。
董少林的感受是,当前AI应用落地需求呈井喷态势,新场景新应用层出不穷。“和企业交流时,他们展示的AI前沿应用常让我们耳目一新。”
事实上,真正的压力可能更多来自对于人工智能应用的认知已经落后于现实。
机遇在于应用
作为深圳市灵动动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王铭宇希望利用人工智能帮助兽医“读片”。“宠物医疗器械市场规模远小于人医,与人医相比落后5到10年,甚至一些器械也比较老旧。因此宠物医疗赛道比较适合初创团队,初创团队就是要在‘小池塘里养大鱼’。”
“国内对于宠物医疗数据的监管与人医不同,因为不涉及伦理审查问题,收据收集不难。但是宠物医疗数据的质量并不高,比如多数X光片没有匹配文字报告,而缺少文本信息的数据无法用于人工智能训练。AI应用于医疗领域不能只输出结果,而是需要像人类医生一样解释,在输出结果的同时输出证据。比如一张显示宠物患有肾结石的X光片,需要将肾、输尿管、结石等信息详细标注,也就是呈现每一种疾病的证据。”王铭宇将数据标注工作形容为“脏活、累活”,这也形成公司的壁垒,公司目前已经拥有这一赛道高质量的数据集。
像这样人工智能在细分领域的应用,正是深圳希望把握的机遇。对于政府在其中的作用,董少林认为需要政府提供产业政策和企业服务。尽管DeepSeek等技术的出现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模型开发成本,但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仍是不小的负担。深圳市已出台“训力券”政策对企业算力支出予以补贴,降低企业成本。同时,南山区设立了专项资金政策,重点支持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有初创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对于初创企业而言,人力成本在成本构成中占据主要位置,而算力成本占比已经达到20%左右,并不算少。”
去年年底,深圳发布“训力券”政策,每年发放最高5亿元“训力券”,降低人工智能模型研发和训练成本。对租用智能算力开展大模型训练的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按不超过服务合同金额的50%,给予最高1000万元资助,对初创企业提高资助比例至60%。
除去补贴算力成本,董少林认为,政府能做的更多是“造势”,比如针对一些场景开展“揭榜挂帅”,目的是吸引人们尝试应用人工智能。
南山区今年推出人工智能“揭榜挂帅”机制,首批10个政府场景已向企业开放。“比如在应急预警领域,我们提供全区的灾害风险数据,企业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来训练灾害预警模型,开发资源配置系统。”董少林透露,下一步将采用“企业出题、企业解题”模式,鼓励更多市场主体开放自有场景和数据资源,“政府愿意与企业共担试错成本”。
“鼓励企业‘放榜’的方案去年已经制定好,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机会发布。去年大模型应用的门槛依然较高,推出类似政策可能会‘打水漂’。去年购买一台200多万元的服务器可能都难以部署大模型,今年部署成本则直接降至20余万元。”在董少林看来,今年是发布“揭榜挂帅”场景更好的时机。
“深圳在这一轮AI产业的机遇在于应用,特别是硬件之上。”深圳科创学院项目中心负责人张涛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明显感受到创业者项目的变化。“创业者更加关注‘AI+硬件’,在硬件产品引入端侧或云端AI功能的尝试越来越多。”
深圳在今年3月3日发布的四份文件中,有一份特别指向人工智能终端产业,提出到2026年,深圳人工智能终端产业规模达8000亿元以上、力争1万亿元。
边缘创智是一家兼顾软硬件的创业公司,目前的产品可以以非接触的方式,监测人的脉搏、呼吸、心率、面部肌肉运动等数据,已经在医院ICU中进行测试。
在公司创始人赵梓合看来,在智能硬件赛道创业,深圳是为数不多的选择。来到深圳创业前,他曾经作为联合创始人在长三角一座地级市参与过一个创业项目,但是最终因为供应链的问题没能继续下去。“虽然长三角制造业发达,但是当地是一座重工业城市,如果创业项目是面向终端消费者的硬件,可能难以在当地找到合适的工厂。”
他的感受是,花同样的价格在长三角某地级市与深圳为产品开模,深圳的速度更快、质量更高。“对于一个创业团队而言,能否融到钱、招到人可能都是次要的,项目起步阶段能不能迅速推进,很大程度取决于城市本身以及周边资源。”
猿声先达联合创始人程逸钧也有同感。猿声先达处于具身智能赛道,自从宇树科技在今年“出圈”后,有地方政府邀请公司迁往当地,在被拒绝后不断拿出新的方案。“对我们而言,深圳吸引力很强,因为本地供应链体系非常强大,我们距离供应商工厂的车程可能在一个小时以内,购买一些零部件时甚至可以通过闪送配送,这在其他城市很难实现。”
在程逸钧看来,这能够极大降低时间成本,而在产品迭代过程中,最耗时的环节并非研发,而是企业需要与上下游企业对接,沟通、物流都需要时间,往往是这些因素卡住研发进度,而深圳在降低这部分时间成本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科创学院也在帮助创业者更好地利用珠三角的供应链。如果学院不出面协调,珠三角一些工厂老板可能都不愿意与一名创业者沟通,也会影响工厂对项目的投入程度,学院在这里的作用是将创业者‘领进门’。”张涛涛告诉记者,比如创业者向学院提出寻找电机厂的诉求,学院就会告诉他们哪几家工厂符合他们的需求,这样的信息非常重要。如果靠自己搜索,他们会发现深圳本地便有上百家电机厂,但并不清楚各家所长,也就难以利用珠三角丰厚的供应链资源。
无论是通过政策降低人工智能应用门槛,还是利用已有的产业链优势,都成为创业环境的一部分。
如何“抢人”?
“深圳的劣势在于本土高校资源较弱,企业在技术研发上不可能单打独斗,必然需要与高校等科研机构合作,这部分资源更多需要企业在深圳之外寻找。尽管深圳也在引入一些高校在内的科研机构,但是仍需时间沉淀。”程逸钧说。
高校资源相对弱势也导致深圳本土原生人才不足,这似乎是深圳创新创业环境最大的瓶颈。其实,包括深圳在内的地方政府面对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时的焦虑最终总会归结于吸引并留住人才,特别是创业者焦虑,尤其不能忽略的是,“杭州六小龙”中的数位创业者都有离开深圳前往杭州的经历。
今年2月底,深圳市政府新闻办曾召开主题为“打造最好科技创新生态和人才发展环境”的新闻发布会,这被视为深圳放出的第一个“大招”,其中将高校应届毕业生来深求职提供免费住宿天数从7天延长到15天等政策引发市场关注。
今年3月底,南山区政府印发《南山区支持创新创业“六个一”行动方案》,其中多条措施涉及对人工智能、机器人人才的招引,如提出“对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重点产业领域初创企业的优秀青年骨干人才,符合条件的给予每人最高60万元奖励支持”。
有深圳本地投资人表示,伴随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一批年轻的创业者正在登场。“他们来自大厂、高校,根据我们接触人工智能企业的经验,其中九成是年轻人,不乏从名校休学创业的案例。”
深圳希望更多吸引到新一代创业者,而相比于人才政策,更重要的可能是创业环境。“像深圳针对不同类别的人才有不同的招引政策,但是其不一定适用于当下。”前述投资人表示,“政府希望通过‘模力营’等孵化器打造创业生态,比如提供免费空间,让创业团队入驻,在创业者不具备造血能力时降低其成本,以此吸引更多创业者。”
“对于创业公司而言,还是希望把钱花在刀刃上。虽然也收到其他孵化器入驻的邀请,但因为需要缴纳物业费,最终还是选择入驻深圳一家可以免费提供场地的孵化器。”有创业者告诉记者,对于团队人数较少的科创公司而言,能否以更便宜的价格找到办公场地至关重要。
深圳科创学院这样的载体也在承担类似的职能,学院的身份是事业单位,由深圳市与南山区两级国资出资成立。
张涛涛告诉记者,科创学院每年通过科创训练营吸引有创业意愿的人来到学院,他们还没有成熟的项目、团队,在学院逐步找到方向。想法成熟后,便会进行预探索期立项,得到资金、技术、导师等多方面支持,团队可以做demo、做调研。随着团队磨合,会进行探索期立项,获得更多经费、独立办公空间,目标是拿到天使轮投资。
“最初,深圳市人才局在支持科创学院项目,一方面希望吸引创业人才,另一方面希望构建创业生态。”张涛涛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前深圳的“孔雀计划”将人才划分为ABC三类,即使是针对全球排名靠前高校博士的C类人才,也需要给予5年180万元补贴,只要符合条件即可入选,基本未经筛选,这是引进人才的常见模式。“其实科创学院每年也帮助深圳引进不少人才,这些人才可能没有名校博士的头衔,但是如果去他们就读的学校了解,会发现他们都是学校最能‘折腾’的人,这可能比一个博士头衔更有价值。”
在他看来,只需要投入几十万元支持他们创业的早期阶段,并将近90%的股份留给创业者即可,这是一件非常“划算”的事情,但是这些人在毕业之初选择到深圳创业,无论是否成功,大概率都会留在深圳,很多地方政府还没有意识到支持创业者的意义。
赵梓合便属于在学校能“折腾”的人。2021年,当时还在沈阳读本科的赵梓合便已参加RoboMaster机甲大师高校系列赛(RMU),作为国内重要的机器人竞技赛事,RMU由大疆创新创始人汪涛发起承办。目前边缘智创的核心研发团队全部有RMU参赛经历,也正是通过RMU,赵梓合了解到科创学院的夏季科创营,并在此后以实习生的身份加入科创学院,探索创业方向。
深圳正想尽办法吸引人、留住人。不过,有创业者向记者坦承,深圳此前的一些政策对于创业者而言还不够友好。“比如我们的一些产品需要做医疗器械设备认证,申请创新性IP,开设相应绿色通道。这样的绿色通道并非全然没有,但是门槛较高,比如企业需要申请成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看并不合算。这可能更适合从高校产学研转化而来的企业,这些团队背靠高校,成本压力也更小。”
他坦言,这些流程可能并非那么复杂,但是还可以更加简化。“深圳有众多帮助企业申报各种资质的第三方公司,他们再从企业获得的补贴中抽成。投资人、客户,或是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打我的电话都可以理解,但是每天有大量这种中介公司打我的电话,这足以说明问题。”
此外,他也希望善于“搞钱”的深圳可以对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多些耐心,诞生更多耐心资本,“深圳的节奏太快,投资方偏爱赚快钱,不愿做长期布局。宇树科技从深圳搬到杭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难以在深圳找到投资,当时投资方看不到四足机器人的盈利前景。但是一些科创项目可能在A轮、B轮融资时都难以确定一套商业模式”。
记者:陈惟杉(chenweishan@chinanews.com.cn)
责任编辑:刘德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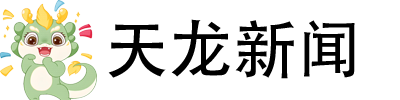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